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动因:制度史解释
司法兰亭会:倡导对法律人的人文关怀,促进法律人的新知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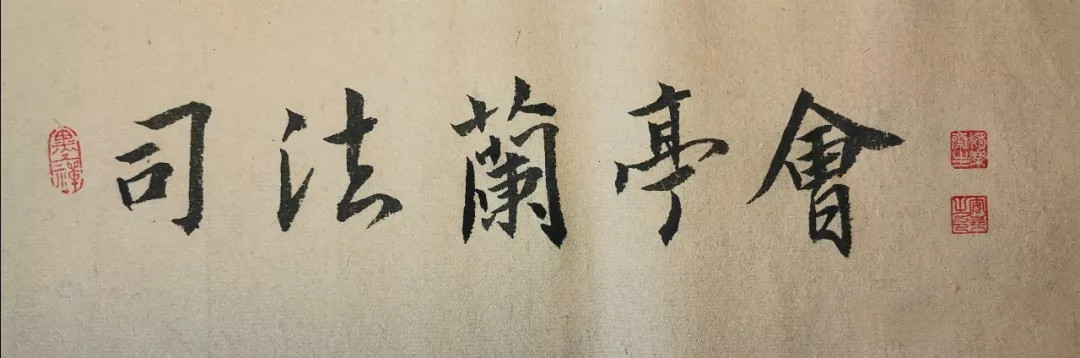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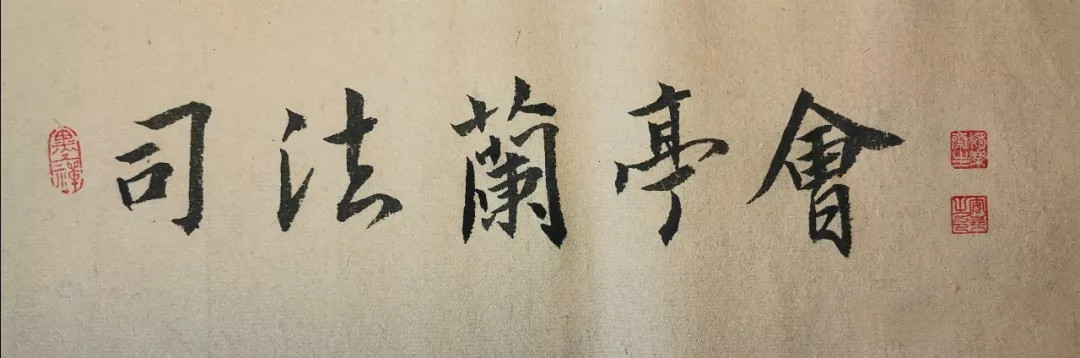
(感谢“独乐斋主”题字)


樊传明,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感谢樊传明副教授特别授权。
落实证据裁判,完善证据制度,是中国司法改革在技术层面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对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建构。从比较法和制度史角度观之,排除规则体系主要是英国司法制度变革的产物。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的一些诉讼程序变动,为以排除规则筛选庭审证据这种管控方式,提供了发展动因。首先,陪审团的转型造就了二元管控结构和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这为排除规则的发展确立了制度空间。其次,证据成为危险性信息源,产生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实践需求。最后,激励对抗式举证和支撑言词论辩式庭审的需要,成为排除规则得以长远发展的程序驱动。对这些发展动因的制度史解释,能够为反思当代中国排除规则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供参照。
一、为什么诉诸外国法史?
在司法审判程序中,一项证据材料可能因为三类理由而被排除,失去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资格。第一类理由是相关性:若一项材料与任何待证事实都不相关,它就不应被采纳为证据。该理由在法律中的体现即相关性规则:“相关的证据具有可采性,除非有相反规定……不相关的证据不可采”;如果一项证据具有使某待证事实“更可能或更不可能的任何倾向性”,它就是相关的。第二类理由是“证明价值-危险性权衡”:即使一项材料与某个待证事实相关,但是假如它所引发的事实认定错误风险(例如误导裁判者的风险、引发偏见的风险、隐藏错误的风险)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证明价值,那么这样的材料也应被阻挡在法庭之外。要求排除文书复印件、不出庭证人的证言、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规则,主要就是基于这类理由。第三类理由是“外部政策”:如果采纳一项证据可能会侵害除发现真相以外的某种法律价值(例如程序公正、人权保障、诉讼效率),则该证据也可能被排除。相对于发现真相而言,这些价值目标是外在于司法证明程序的,因此被称为外部政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证特免权、逾期举证衍生出的证据排除效果,都是根据外部政策理由。这类排除规则被称为“外部政策规则”,基于前两类理由的规则被称为“证明政策规则”或“内部规则”。
第一类相关性理由,尽管已写入法律文本,但实际上是一个基础性的逻辑要求。排除与待决事项不相关的信息,这一规则几乎无需由法律创设,也无需对此提供逻辑之外的理由。第三类外部政策理由,反映了法律在不同价值目标之间的权衡,即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为保护其他目标而限制对事实真相的调查。尽管现代各国的法律在具体情境下的价值权衡结果会有差异,但是做出这种权衡本身而且将其制度化,是不可避免的。基于外部政策理由而设置的排除规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广泛存在。第二类理由则具有非常明显的技术化特征,因为它预先对具有证明价值的信息进行筛选,人为地限缩了法庭事实认定者能够接触和使用的证据范围。这就使得法庭事实认定活动明显区别于日常经验型的事实调查方法:不是考虑所有相关的信息,而是只考虑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这种做法虽然在普通法系源远流长,却不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青睐。即使在英美证据法理论中,对于这种立法政策也不无质疑。最著名的就是边沁的“反规范”理论,他认为“证据是正义之基:排除证据,就排除了正义”。当代英国证据法还呈现出简化这类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
所以,根据“证明价值-危险性权衡”理由而排除证据的规则,其正当性需要论证。在普通法系,批评和主张废除这类规则的声音,与为这类规则辩护的声音都存在。尽管英国证据法正弱化这类规则,但是在其他普通法系国家,这类规则仍具有牢固的立法地位。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如何证成这类排除规则,不仅是一个比较法理论问题,而且有现实意义。通过完善证据立法和落实证据裁判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和实现严格司法,是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而完善证据立法和落实证据裁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排除规则体系的完善和适用,包括对相关外国法规则的借鉴和移植。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在我国当下的法学语境中,一种以移植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各项规则为标志的‘变法运动’正逐渐成为证据法学研究的主流倾向。”在关于证据立法的学者建议稿中,对英美证据排除规则的移植也是一个重要部分。而且现行中国证据制度已经确立了一些这样的排除规则。既然当代中国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倡导这类排除规则,就引出以下问题:证据排除规则或者说通过排除证据来促进法庭事实认定的立法策略,其发展动因是什么?是哪些因素引发了这类规则,从而也为这类规则提供了功能上的正当性?
本文尝试从外国法制史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从制度史来看,“内部”的或者说服务于“证明政策”的排除规则主要是英国诉讼程序变革的产物。十八世纪中后期至十九世纪初的英格兰是现代普通法系证据法的发源地,它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英美证据法的现代样态,即以内部排除规则为主导性规范的体系。因此可以假设:当时的诉讼程序环境为排除规则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因。对这些发展动因的考察和分析,将会有助于理解内部排除规则的客观功能和运行条件,从而为当代中国的制度改革和法律移植实践提供参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页历史就抵得上一卷逻辑。”就诉讼法这样一个分支而言,考察规则的发展动因尤为重要。拉德布鲁赫如此描述诉讼法的特性:“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如果不能理解某个诉讼法规则背后的发展动因,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其功能,也不可能为该规则的移植和立法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司法程序的变动,从以下三个方面解释内部排除规则的发展动因:第一,排除规则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空间,即何种司法程序构造使得排除规则的发生是“可能的”。第二,排除规则旨在回应什么实践需求,即司法实践中的哪些现实因素使排除规则是“必要的”。第三,排除规则的长远发展有赖于什么样的程序驱动机制,即何种诉讼技术性特征可以为排除规则的发展提供持久而强劲的动力。由于内部排除规则是英美证据法的主体性规范,所以考察这类规则的起源也就是讲述英美证据法的故事。英美学者经常将证据法的起源和发展与陪审团制度、对抗制程序相关联,从而确立了两种阐释证据法的路径。本文将首先对这两种路径进行描述,分析其中的疏漏和矛盾,然后展开本文的解释。最后一部分回到中国司法改革背景,分析和展望中国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
二、陪审制、对抗制与证据法
(一)十八世纪的证据法转型
关于证据排除规则的起源和发展,美国证据法学家威格莫尔提供了一个时间线。他认为这些规则应追溯至英国都铎-斯图尔特(Tudor-Stuart)时期,即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这个时期,证据排除规则随着“指示型陪审团”这种审判模式的发展而逐渐得以确立。“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见证了许多排除规则的逐渐增长,这些排除规则将各种类型的证据排除在外。这一增长趋势在十九世纪早期有快速和复杂的扩张。”但是直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对这些庞杂的证据排除规则才有了正式的书面记载。因为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初审法院报告(nisi prius reports)制度,为排除规则提供了书面载体。在此之前,这些规则“主要存在于经验丰富的庭审律师精英的记忆中,以及存在于法官的即时裁量中”。
威格莫尔关于排除规则发展时间的描述,曾被英美学者普遍接受。但是当代法制史学家郎本质疑了威格莫尔的观点。郎本主要通过考证三个法史文献,而对英国证据法进行类似于断代史的研究。第一个文献是“老贝利审判实录”。位于伦敦老贝利街(Old Bailey)的中央刑事法院(Central Criminal Court),负责审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重大刑事案件。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两个世纪里,连续出版了一套被称为“老贝利审判实录”的报告,记录老贝利法庭审理的案件。它最初只是民间出版的大众读物,后来逐渐发展为准官方性的法律报告。第二个文献是瑞德法官的笔记。王座法庭(King's Bench)的法官达德利·瑞德(Dudley Ryder),在1754至1756年间审理案件过程中,对于法庭上的证据和论证做了大量笔记,以备在审判结束时为陪审员概括证据和做出指示。第三个文献是吉尔伯特的《证据法》。吉尔伯特爵士曾担任英国财政法院首席法官,他于1720年左右完成(但直至1754年才出版)的《证据法》一书,被认为是十九世纪之前最为重要的证据法专著。郎本的考证反映了十八世纪初至八十年代英国证据法的样式。它表明当时所适用的英国证据法具有以下结构性特征:
第一,偏好书面记录形式的证据,强调书面文件的真实性。在当时具有基础性地位的最佳证据规则,实际上是督促当事人记录法律行为且提交书面证据的规则。吉尔伯特的著作将最佳证据规则表述如下:“与证据相关的第一个也是最为显著的规则就是人类必须拥有事实性质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的证据,因为法律的设计就是为了获得对权利问题的严格证实,没有了事物性质所能允许的最佳证据,也就没有了对某个事实的证实。”在这样一个抽象规则之下,吉尔伯特比较了各种证据的优劣,建立起一个形式化的证据层级。在这个层级中,书面记录优于口头证据;在各种书面记录中,公共记录(如立法机关和王室法院的法律文件)处于层级的顶端。可以看出,吉尔伯特的著作所反映的英国证据法,是以书面证据为核心的,“司法过程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决定性的书面证据。”郎本分析瑞德法官的笔记后,得出了相似结论:“早期的证据法几乎完全是在关注关于书面文件真实性和充分性的规则。在达德利·瑞德之前民事审判中的证据法实践,主要是关于书面证据的问题。”不过这种对书面文件证据的偏好,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中。十八世纪的刑事诉讼则是一种“争吵式”或“被告人陈述式”审判,要求被告在法庭上对指控做出回答和陈述。但被告又缺乏证人资格,不能进行宣誓,不能由律师代言。所以当时的刑事诉讼又不是现代的言词审判方式。
第二,证据法设置了严苛的证人资格规则和宣誓规则,但是不注重对证人的当庭审查和交叉询问。以证人资格为关注点的规则,不同于现代的各类证言排除规则。在吉尔伯特的著作中,关于非书面证据的内容,主要是论述与诉讼结果有利益关涉的人不具有证人资格。瑞德法官笔记与此类似:“以具有利益为由反对证人作证,在瑞德的民事笔记中占据显著位置。”这种以存在利益关涉为由否定证人资格的做法,大大缩小了潜在证人的范围,与现代宽泛的证人资格规则迥异。尽管当时也存在类似传闻排除规则的判例和论述,但是排除传闻的理由是证人“未宣誓”,而不是“未经交叉询问”这一现代理由。尽管在当时的理论著作和案例报告中已经出现对传闻证据的批评,但实际上传闻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被频繁使用。郎本认为,“瑞德笔记没有迹象表明,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存在着类似现代传闻规则的东西。”
第三,存在非正式的法官评论、概括、指示等实践,它们是法官影响和控制陪审团评议的常规方式。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员退庭评议之前,法官可以和陪审团进行非正式的交流,借此将自己的见解灌输给陪审员们;当陪审员结束评议、给出裁决的时候,法官能够通过询问而获知他们的裁决理由;法官还可以拒绝陪审团给出的裁决,与陪审团争辩,给出进一步的指示,要求重新评议。这种控制陪审团的权力也存在于民事诉讼中。瑞德法官的笔记显示,在很多民事案件中法官会发表对于案件事实的看法,而陪审团会遵从法官的意见。“研究瑞德的民事审判,人们会得出这样的印象:法官常规性地控制着陪审团的裁决。他将陪审员引向自己关于事实和法律的观点,似乎他与陪审员之间存在一种非正式的、对话式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能够‘侵入陪审团的心理’——如果他认为陪审团倾向于背离自己的意见的话。”如果我们将排除规则与法官的评论、概括和指示作为两种不同的管控陪审团的方式,那么可以说,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排除规则尚未成为一种常规化的管控方式,而法官的评议、概括和指示则非常地频繁。这与现代英美证据法截然不同。
第四,尽管存在现代排除规则的影子,但它们是裁量性的例外,而且与现代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和功能有明显差异。威格莫尔所追溯的那些排除证据判例,以及郎本在上述文本中找到的排除判例,是法官在具体个案中行使裁量权的结果,不是常规性做法,远未形成刚性的和一般化的规则。而且即使将它们称为“规则”,也与现代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有别。例如排除传闻的理由不是无法当庭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而是欠缺宣誓这一形式要件。而且,这些排除“规则”并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庭审信息阻隔机制。按照郎本的考证,当时的法官通常是在陪审员在场的情况下裁决证据是否可采纳,不会采取措施防止陪审员听到该证据;当时出版的法律摘要还表明,对于传闻的异议应当影响可信性而不是可采性。相比之下,现代排除规则严格区分可采性与证明力,它们将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过滤掉,而且要求采取措施保证陪审员不会知悉该证据的内容;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之证明力,则保留给陪审员判断。
上述分析表明,在十八世纪中期尚未形成现代的证据排除规则体系。但是在此之后,品格证据排除规则、非自愿口供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等典型的排除规则,逐渐得以确立。郎本对排除规则历史的定位似乎比威格莫尔的定位更晚一些,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可以兼容。威格莫尔的写作目的是通过梳理各条证据规则的历史先例,建构证据法教义学体系。他承认在十八世纪之前出现的是现代证据法的“轮廓”,而不是成型。郎本旨在对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证据法宏观结构进行描述,分析是否已经形成了现代的规则体系。但这种结构和体系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存在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不管是威格莫尔、郎本还是其他的英美证据法史研究者,对于以下描述都是没有争议的:
“以当庭证人的口头证言为核心的现代证据法,在十八世纪末以及贯穿十九世纪的时间里,取代了旧式的证据法。现代法舍弃了将偏好书面文件的最佳证据规则作为证据法组织性原则的努力。交叉询问替代宣誓,成为采纳口头证据的基本保障。废止了以关涉利益为由使当事人不具有证人资格的能力制度,也使传闻规则具备了最终的特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宏观的结构性层面上,现代证据排除规则体系主要是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的产物。或者说,英国证据法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经历了以下转型:从通过法官的指示等方式来规制“证明”,转型为通过一般性法律规则来规制“证据”;从根据最佳证据原理寻求“好的”证据,转型为根据证据排除规则过滤掉“坏的”证据;从证据层级理念、证人资格规则等反映出来的形式理性标准,转型为重视言词证据和交叉询问程序的实质理性标准;从法官的个案裁量性实践,转型为对刚性法律规则的适用。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转型,才演进出现代的英美证据法模式。
(二)关于证据法动因的两种解释路径
为什么证据法会经历上述转型?一种解释是,现代证据法是英国陪审团审判的产物;另一个解释是,现代证据法源于英国对抗制。这两种解释路径尽管抓住了证据法的某些发展动因,但它们都是比较粗糙的制度史叙事,而且有内在矛盾。
1.证据法是陪审制的产物?
美国证据法学家塞耶认为,证据法的起源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存在密切关联。师承塞耶的威格莫尔,在撰写其证据法巨著和建构证据规则教义学体系时,重申了这一命题:“我们的可采性体系是基于以下目的而设立:防止陪审员被特定种类的证据所误导。”这种解释中包含着对陪审团的强烈不信任。有学者认为,由法官适用排除规则过滤掉某些证据,约束陪审团的事实认定活动,这体现了一种“家长式”观念。这种解释路径成为英美证据法理论中的传统和主流观点。即使现代陪审团审判所占的比例已经非常小,规制陪审团的需要仍是阐释证据法的基础性原理。例如,当代证据法学家罗纳德·艾伦在其证据法教科书中,仍然将证据法的价值与陪审团相关联:“大多数证据规则的政策含义,是基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确定的,即:允许陪审团考虑这种类型的信息,会对争端的公正解决产生什么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证据法和陪审制之间的关联,塞耶和威格莫尔等人主要关注“法律外行裁判”这一特征,即认为:为了防止作为法律外行、缺乏审判经验的陪审员被误导,才需要由法官适用排除规则过滤某些证据。这种解释也被称为“控制陪审团”理论或“不信任陪审团”理论。但是对于证据法与陪审制之间的联系,还存在其他视角,可以聚焦于陪审团审判的其他特征。例如,达马斯卡在将英美证据法与大陆法系证据制度相比较时,就强调了陪审团审判所造就的二元式法庭结构特征。
认为证据法是陪审制的产物这种解释路径,存在一些矛盾。首先,英美陪审团制度可以追溯至十二世纪的王室证人和指控陪审团制度。这种制度经过了一系列演变,到十六世纪已完全发展为现代的陪审团形式。但是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中期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却没有发展出现代英美证据法体系。将证据法仅仅归因于陪审制,无法解释这一时间上的错位。其次,英美陪审团制度是建立在“陪审员有能力解决关于证据分量或证明价值的问题”这一假设之上。如果过分强调陪审员的证据评价能力缺陷,就与陪审制的潜在假定相矛盾。这种逻辑矛盾无法为证据法提供充分的正当性基础。最后,即使不考虑前述时间上的和逻辑上的矛盾,陪审员是拙劣的事实认定者,因此应当由法官进行“家长式”的管控这一假定的真实性,也有待检验。实际上,许多认知科学研究和实证研究表明,作为个人的陪审员,以及作为集体的陪审团,在认定案件事实这方面,具有很多相对于法官的决策优势。这些研究倾向于证伪前述假定。因此,对于证据法与陪审制之间的关联,应当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对于法律外行的裁判需要通过证据法规制”这一粗糙的解释上。
2.证据法是对抗制的产物?
从对抗制的角度解释证据法的起源和功能,这一路径的开创者是美国证据法学者艾德蒙·摩根。他认为,“既然我们制度的对抗式特征和它对陪审团的使用一样独特,那么最好不要不加审视地接受这一老生常谈:是陪审制导致了我们的证据法的产生和存续。”他主张从对抗制的角度理解证据法。对抗制解释实际上强调了律师在司法证明程序中的角色。他们发挥着收集、保存和提交证据,以及主导法庭调查、言词辩论等非常重要的职能;但是他们又服务于自己的当事人,具有强烈的追求胜诉动机。因此,律师的行为经常偏离司法证明程序所追求的发现真相目标。证据排除规则就是为了规制律师的行为。如果说传统的解释路径强调“控制陪审团”,那么这一解释路径就是在强调“控制律师”。从对抗制的角度解释证据法,最著名的现代理论版本是戴尔·南斯的最佳证据原则。南斯认为,虽然对抗制本身具有激励诉讼双方举证的功能,但这种激励功能有时会失灵——它只能激励诉讼双方提交胜诉策略上的最佳证据,而不一定能激励他们提交认识论上的最佳证据。因为对抗制在激励举证方面会失灵,所以需要另外确立最佳证据原则,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各种排除规则,以弥补对抗制的不足。
认为证据法是对抗制的产物这一路径,尽管非常有解释力度,但仍然存在问题。郎本对英格兰法制史的考证表明,现代证据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出现要早于民事诉讼,但是对抗制结构在民事诉讼中的出现要远远早于刑事诉讼。“如果对抗制程序确实导致原有的控制陪审团结构破裂,并且导致产生了包括证据法在内的新的工具——这一理论在刑事诉讼中显得非常有魅力——那么一个难题就是解释:为什么证据法没有在民事诉讼中出现得更早?”这一时间上的不对称,使我们难以将证据法的起源简单地归因于对抗制。实际上,“对抗制”这一术语及其所代表的类型(模式)研究进路,因过于宏观而有失精确。对抗制这一概念包含了许多要素特征,对抗式举证只是其中之一。究竟哪些要素特征与排除规则之间存在何种具体关联,需要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前述两种解释路径当然不是毫无价值,但是过于宏大和粗糙,需要细化论证、重组论据和调整叙事方式。基于前文所确定的时间线,可以提出假设: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英格兰司法程序为排除规则提供了可能的程序环境,因此才有了例外性、裁量性的证据排除先例。但是还缺乏强劲的动力,因此在漫长的时间里没有发展出一般和刚性的排除规则体系。在此之后的某些变化,则为排除规则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因此催生了现代英美证据法。下文将按照这一顺序展开论述。
三、二元管制结构中的劣势事实认定者
证据排除规则是一种对司法事实认定活动的常规化、一般性管制方式。因此,只有当存在“管制者-被管制者”的二元法庭结构,而且管制者处于某种能够实施管制的优势地位时,才可能生成证据排除规则。英国诉讼程序从引入陪审员开始,经过了漫长渐变,才形成这种二元管制结构,为排除规则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一)事实认定的二元管制结构
现代研究者已经注意到陪审制的结构性特征与排除规则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英美的陪审团审判形成了法庭上的分工:陪审员们独立、终局地负责事实认定问题,法官负责法律适用问题以及程序管理问题。因为存在两个裁判主体,所以这是一种二元式法庭结构。在事实认定问题上,它具体表现为“管制者-被管制者”结构:尽管陪审员是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法定主体,但是法官可以通过其程序管理权筛选进入法庭的证据,从而间接管制陪审员的事实认定活动。这种管制结构是英国陪审团历史发展的结果。
陪审团的最早萌芽形态是王室证人和指控陪审团。在英国司法制度发展之初,普通人就被引入审判程序。国王在调查案件的时候,有时会召集一帮“证人”,帮助王室收集信息、查明罪犯。王室证人所承担的角色,实际上是调查员兼证人。该王室证人制度起源于什么时候、什么地域,尚存在争论。在十二世纪,王室证人逐渐具备了新的职能——提出指控。王室要求由一些普通居民以团体的名义提出指控,即所谓的“指控陪审团”(jury of presentment)。国王亨利二世于1166年颁布的《克拉伦登宪章》中,载有对这种指控陪审团的描述:“在所有郡和百户,必须由每百户的12名以及每村镇的4名较为守法之士展开调查;他们要宣誓说出真相,即在他们的百户或村镇内是否有任何被指控或者臭名昭著地涉嫌为强奸犯、谋杀犯、盗窃犯或者窝藏前述罪犯的人”。
由王室证人演变而来的指控陪审团,实际上兼具调查员、证人和控告人的职能,这种形态显然与现代陪审团相去甚远。指控陪审团不是在法庭上与法官分工协作、独享事实认定职权的裁判主体。只有当指控陪审团发展成所谓的“知情陪审团”(self-informing jury)之后,二元式法庭结构才得以形成。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一方面作为替代神明裁判的审判方式(实际上也反映了世俗王权与教会之间对审判权的竞争),另一方面作为国王与封建领主争夺审判权的手段,承担裁判职能的陪审团作为王室司法权之表征而登场。在1220年左右,法官要求指控陪审团不仅提出控告,而且还必须宣布被告有罪还是无罪。从此陪审团具备了裁判职能,有学者将这一发展称为陪审团的“司法化”。指控陪审团演变成兼具调查员、证人、事实认定者职能的陪审团形式。
这种新的陪审团职能混杂,但核心职责是裁决事实。由此,二元式法庭得以形成:职业化的法官解决法律问题,临时召集的陪审团解决事实问题。但是法官的职责不限于适用实体法,而且还扮演着程序管理者的角色:法官可以对证据发表评论,对证据的内容进行概括,对陪审员做出法律指示等。所以陪审团和法官之间不仅是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分工关系,而且还存在事实问题上的管制关系。从逻辑上来说,这种二元管制结构对于排除规则的发展不可或缺。假如没有这种管制结构,作为一般性管制手段的排除规则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是二元结构的存在也不必然要求管制。假如陪审团被认为是非常优秀的事实认定者,而且比法官掌握着更多的信息资源,那么法官就不可能对陪审团实施管制。或者说,只有当法官相比于陪审团处在一个优势位置上,排除规则这种管制手段才会具有充分发展空间。
(二)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
1.对陪审员认知能力的假设
对陪审员认知能力的拙劣假设,或许可以解释法官的这种优势管制地位。正如“证据法是陪审制的产物”这个命题所说明的那样,由于陪审员是未受过法律训练、没有司法实务经验的外行,因此在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时候更容易犯错误,需要由专业的法官进行管理和指导。以下论述反映了对陪审团的不信任:“在陪审团里面我们拥有的是经验不足的新手……我们训练新兵打仗,我们给律师、内科医生、牙医、助产士、兽医、马蹄铁匠和司机颁发执照,但是,只要一个人能说任何一种英语、听力正常、在候选陪审员名单上并且没有成见,他就被认为是在法庭上解决纠纷的合适人选”。当然,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关于陪审员认知能力的这种假设,实际上不是普遍存在;如果它普遍存在的话,就会与陪审制的久远历史以及由陪审员认定事实的传统相矛盾。不过,这种批评也存在问题。采用陪审团制度未必是基于对陪审员发现事实真相之能力的认可,而很可能是因为其他的社会、政治或宗教原因。为了发挥陪审团制度的其他价值而容忍其在认知能力上的缺点,这是可能的。从塞耶、威格摩尔以及当代许多英美证据法学者的论述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前述认知能力假设是普遍存在的。当然,存在这种假设是一回事,该假设符合实际是另一回事——后者有待更多的实证性研究来检验。
尽管如此,通过比对排除规则的历史与陪审团的历史可以发现,对陪审团的这种认知能力假设不足以创设一个需要施以管制的劣势地位。因为,由法律外行担任常规性的法庭事实认定者,滥觞于1220年左右形成的知情陪审团制度。但是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才出现排除规则的影子,而直到十七、十八世纪才“见证了许多排除规则的逐渐增长”。为何排除规则的发展会远远落后于陪审团的发展?很可能是因为,陪审团的“知情”形态使其处在一个相对于法官的信息优势地位上。这种陪审团制度模式中不存在排除规则的空间。
2.非知情裁判模式
知情陪审团制度是从发生犯罪的狭小区域内挑选可能了解案情、熟悉嫌犯的人,或者更方便收集这类信息的人作陪审员。因为陪审员是犯罪地的居民甚至嫌犯的邻居,他们很可能预先知晓许多与案件相关的信息;他们可以亲自到庭外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而不是作消极的裁判者;他们对事实的裁决不受法庭上提交的证据的限制,可以主动向“那些消息灵通但未被传唤出庭的人士”咨询。这些特征说明,当时的陪审员在掌握案件信息方面,处于相对于法官的优势地位。郎本的描述反映了知情陪审团的上述特征:“这种中世纪的陪审员来到法庭上,与其说是来‘听’,不如说是来‘说’,与其说是来听审证据,不如说是来给出已经预先形成的裁决。”威格摩尔也给出了相似的描述:“当法官组织陪审团协助他们调查时,一开始陪审员能够自由而不受拘束地使用证据(除了一些关于文件的规则)。他们可以使用自己在所居住的地方形成的印象,他们甚至还可以到法庭之外走访邻居们询问消息。”对于这种陪审员,法官是不必管制、也无法管制的,因为他们掌握了比法官更多的案件信息来源。这种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让陪审员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积极地开展事实调查活动,而不是让他们在法官的精心控制下消极裁决事实。
在十六世纪,英国陪审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由知情人士组成陪审团,而是使用“像白纸一样”预先对案件事实毫不知情的人作陪审员。他们“既不认识原告也不认识被告,仅仅基于提交给他们的证据裁决作为抽象主张的争议事实”;组成陪审团的那些人“之所以被挑选,不再是因为他们对事件有所知悉,而是被期望对于该事件是无知的”。陪审员由来自临近区域的积极调查者转变为消极的审判者。这种变革使得陪审员的角色变得单一,调查员、证人的职能被剥离,只保留了事实裁决者的角色。而且,陪审员被禁止开展庭外自主调查,只能根据法庭上呈现的证据信息(主要是证人证言)裁决案件。“频繁使用的证人,成为陪审员的主要信息来源”。“当庭证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信息手段(应该是在十六世纪后期),陪审员自己的‘知识’就发挥了次要的作用。最终,到十七世纪末,陪审团不再被认可和允许掌握在法庭上提供的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这是一个完全的功能转变。”
上述转变缔造了现代的陪审团形式,即“非知情人裁判”模式。从知情陪审团到非知情裁判模式的转变,使陪审员们失去了原有的信息优势地位。相对于这种消极的法庭事实认定者,作为诉讼程序管理者的法官则取得了优势地位。他们比陪审员接触到更多的具体案件信息,更加熟知案件事实的一般规律,也更为清楚司法程序对于原始案件事实带来的一些扭曲效应。至此,与前述对法律外行认知能力的拙劣假设相结合,非知情裁判模式塑造了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从而为法官通过证据排除规则管制陪审团创造了空间:“对于有经验的法官而言,这意味着未在评价证据方面受到训练的陪审员必须得到指导。”这种解释与前述排除规则和英国陪审制发展的时间线是契合的:非知情陪审团的逐渐形成是贯穿十六世纪的法制史事件,而排除规则的萌芽和零星出现发生在英国都铎-斯图尔特王朝时期,即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
四、对危险性信息源的管控方式
尽管英国诉讼程序早在十六世纪就为排除规则创造了生长空间,但没有导致排除规则的迅速发展。这种空间只是说明了管制事实认定者的可能性,但不意味着实施管制的必要性。十八世纪英国诉讼实践中的一些变化,使得某些证据成为具有显著危险性的信息源,从而为排除规则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传统的管制方法式微,进一步凸显了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一)具有显著危险性的信息源
十八世纪的英国诉讼程序有一些较为微观的变化,使得提交到法庭上的证据经常具有显著危险性,包含着极大的错误风险。第一个变化是赏金猎人制度。当时的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以赏金的方式奖励那些逮捕和成功控告罪犯的人。有时也采取发布悬赏公告的方式,或者让提供犯罪信息的人分享对罪犯的罚金。这样的制度为鼓励民间志愿者参与刑事执法提供了经济上的诱因,但同时也鼓励了伪证。从三十年代开始,为获得赏金而诬告或作伪证的案件丑闻不断爆出,困扰着刑事司法程序。第二个变化是对污点证人角色的频繁使用。为了鼓励共犯作证,治安官或大陪审团可以对那些同意指证犯罪同伙的人,免于起诉或给予赦免。这样的制度尽管可以鼓励共犯证言,提高追究犯罪的力度,但是与赏金猎人制度一样,在实践中也鼓励了虚假证言和捏造证据行为。当时的很多案件都显示了污点证人的不可靠性。
因为上述变化,进入审判程序的证据信息经常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相关的证人具有撒谎的动机,为了将被告人定罪而试图欺骗法庭,他们提供的实物证据也可能是伪造的。这些证据引发了许多判决被告人有罪的错案:“在十八世纪(刑事证据法规则主要在这个时期形成),英国的司法体制被错判无辜被告人有罪的丑闻所困扰,这些错判是基于证人虚假的证言而做出的。”为了防止这些具有危险性的证据信息导致错案,法官采取了包括排除特定证据在内的一些管制措施。美国学者伊姆温克里德教授(Edward Imwinkelried)也注意到危险性信息源与排除规则之间的激发关系。他认为,证据法(排除规则体系)主要是为了解决证人伪证问题,对虚假证言的警惕是贯穿英美证据法始终的一个主题。规定证人资格的规则、要求证人宣誓的规则、要求对文书证据鉴真的规则、关于坏的品性证据的规则、意见证据排除规则以及传闻规则,实际上都是为了察觉和防止证人撒谎。伊姆温克里德认为,十八世纪控方的行为是导致虚假证言的主要原因,因为控方给王室证人(Crown witnesses)和职业抓贼者(professional thief catchers)报酬,让他们指控被告人。这种实践做法鼓励了虚假证言。
实际上,郎本所考证的上述两点具体变化,以及伊姆温克里德的进一步分析,都以十八世纪的英国刑事审前调查程序为背景。当时的调查程序主要依赖私人化的、具有偏向性的主体搜集和提交证据。虽然起诉状要以国王的名义提出,但由犯罪的被害人或者其亲属、验尸官充当起诉人,而他们并无律师代理。之所以采用这种自诉制度,是因为可以避免供养和管理公诉机构的棘手问题。直到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英格兰才设立了统一的警察制度。在十八世纪的刑事诉讼中,控方的调查、起诉活动都由私人主体承担。但是也存在一套帮助私人控告者进行诉讼准备的审前程序,即“玛丽式审前程序”:基层治安官(处理治安事件的法官)帮助公民提起控诉,他有权发布搜查和逮捕令,可以羁押被告人;治安官在逮捕嫌犯后,应当讯问嫌犯以及询问扭送嫌犯的人,将这些内容记录在案;治安官有时会就审前调查的问题出庭作证;治安官还可以强制自诉人出庭作证,使当时的自诉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概言之,治安官的角色是为自诉提供支持和监管。不过治安官是控方的支持者而非真相的探寻者,“玛丽式审前程序”明显偏向控方。治安官大多由热衷公共事务的地方士绅担任,他们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官员。所以,“玛丽式审前程序”以及治安官角色的存在,没有使审前调查程序转变为由职业化公共机构主导的模式。私人化的调查和控诉主体,无论在专业性、中立性还是自律性上,都明显低于以国家财政支撑的警察和公诉机构。公共调查和控诉机构的缺位,是加剧证据信息危险性的一个制度性原因。
(二)各种管制方式的比较优势
为了应对上述错案风险,作为程序管理者的法官需要采取有效的管制手段。排除规则可以成为一个信息筛选机制,将那些危险性超过证明价值的证据阻隔在庭外。但是,为了管控危险性信息,适用排除规则不是法官的唯一选择。如果相对于其他管控方式,排除证据不具有足够优势,就很难发展为普遍的、刚性的规则体系。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诉讼程序中,除了排除证据的做法,还有以下管控司法证明(即管制陪审员)的手段。
首先,法官在证据展示程序中有非常积极的角色,可对陪审员的证据评价活动进行事前管制。当时的刑事审判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抗制模式,不是由律师展示证据、询问和交叉询问证人。“在法庭上采纳和提出证据都由主审法官主导,他还询问证人和嫌犯,并对其作出的证言进行评论”;法官帮助控方“尽可能清晰而简洁地说明事实,提出问题,以揭明最有力的被告罪证”。法官不仅帮助控方展示证据,还帮助被告人来质询控方的证据。因为聘请律师提出法律抗辩的被告人很少,所以法官要主动审查刑事起诉中的漏洞。在当时一个案件中,法官告诉被告:“法庭……会确保你不会因为不懂法律而遭受冤屈;我是说,我们就是你的律师。”可见,法官一方面会帮助控方更清楚地展示证据,另一方面也会帮助被告人去质疑这些证据。也就是说,在向陪审团展示证据的环节,法官是深度介入的。这种介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危险性信息源带来的问题,可以看作是一种对陪审员认定事实的管控手段。
其次,法官通过评论和概括证据,可以直接参与认定事实的过程,从而对陪审员的证据评价活动进行事中管制。法官评论(Judicial comment)和法官概括(Judicial Summary)这两种干预陪审员事实认定活动的方式,在现代英美证据法中仍然存在,但属于较为边缘的管控方式。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司法程序中,法官则普遍适用这种方式。刑事审判法官会经常性地与陪审员交流,将自己对于证据和事实的见解告诉陪审员;民事审判法官更是如此:“法官常规性地控制着陪审团的裁决。他将陪审员引向自己关于事实和法律的观点,似乎他与陪审员之间存在一种非正式的、对话式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能够‘侵入陪审团的心理’——如果他认为陪审团倾向于背离自己的意见的话。”法官对证据的评论和概括,直接地影响着陪审员对于证据证明力的评价。
最后,法官还可以舍弃陪审团的事实认定结论,对陪审员的证据评价活动进行事后管制。在现代英美陪审团审判中,陪审员们通常只是做出一般性的裁决,不需要给出裁决理由;陪审员的裁决通常具有终局性,不会被法官通过上诉审等程序推翻。但是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官实际上享有获知陪审员裁决理由以及推翻陪审员裁决的权力。当陪审员结束评议、给出裁决的时候,法官可以询问他们做出裁决所依据的理由;法官可以与陪审员争辩,拒绝他们已做出的裁决;还可以给出进一步的指示,要求陪审员重新评议案件。这说明陪审员的裁决不具有终局性,受到法官的事后管制。
在上述多元化的事实认定管控系统中,证据排除规则一开始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十八世纪末呈现的发展趋势是,与排除规则形成竞争的其他管制方式逐渐衰微,而排除规则逐渐强化。这与英国司法制度的宏观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英国诉讼程序中的律师角色得以强化,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对抗制模式。而且英国的陪审制也在进一步发展,逐渐强化了那些现代陪审制的典型特征,例如一般性裁决、裁决终局性等。在这一诉讼程序变革的背景中,法官在证据展示中的积极角色、法官否决陪审员裁决的做法逐渐失去正当性,因为它们与对抗制、陪审制的发展趋势背离。法官通过评论证据和概括证据来指导陪审员的这种方式也变得更为缓和,因为它与法官和陪审员的分工存在紧张关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职权归于陪审员,而不是法官。法官只能寻找更为间接的管制方式,尽量避免直接侵夺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职权。
除了这些宏观诉讼结构变迁的原因,还有一些较微观的理由,使排除规则更受法官青睐。首先,对于那些非常具有误导性的信息,排除证据这种信息阻隔方式是最为有效的管制手段。就像威格摩尔所评论的那样:“诚然,有的时候通过法官的评论或者说‘概括’来指导他们。但是还需要比指导更甚;需要确立仅针对证据可采性的限制性规则,以阻止陪审员被不相关的东西、偏倚的或欺骗性的证言或者他们自己的情绪、同情心和偏见所误导。”其次,组织证据展示、做出评论和概括、否决事实认定等其他管制方式,难以上升为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只能在具体案件中由法官个别化地适用。而排除证据这种管制方式,可以通过将证据进行类型化界定,从而上升为一般性规则。法官在大部分案件中只需要适用预先设定的规则就可达到规制目的,不需要逐案做实质性的裁量、权衡。所以证据排除规则的总体运行成本可能更低。最后,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初审法院报告(nisi prius reports)制度,法官排除证据的判例和理由通过该制度而累积。这为排除规则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因为这些原因,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诉讼程序中,证据排除规则发展成一种最为重要的管制司法事实认定的工具。
五、对抗式举证与言词论辩式庭审
陪审员成为二元法庭结构中的劣势事实认定者,排除证据成为对危险性信息的最佳管制方式,这为排除规则体系的发展创造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排除规则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初具规模。但是其长远发展和不断完善,仍有赖于一些更微观的、技术性的驱动机制。英国诉讼程序中对抗制因素的加强满足了这一要求。一方面,对抗式举证陷入“自由市场失灵”困境,亟须以排除规则激励举证。另一方面,言词论辩式庭审导致了对证据和推论进行原子式的拆分,还要求通过“异议-裁定”机制组织庭审论辩过程。这使排除规则的适用更细致、刚性。对抗制的技术性特征不仅为排除规则提供了长久驱动力,而且使排除规则的功能扩增:从管控事实认定者扩展为管控对抗制律师,从信息筛选机制扩展为信息激励机制和论辩程序规则。
(一)英国对抗制程序简史
尽管排除规则与对抗制之间的关联很早就被证据法研究者注意到,但是两者的具体关联方式仍有待清晰论述。为了更详细地分析这种关联,需要简要描述英国对抗制的发展,理清时间线以及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差别。
1.英国刑事诉讼中对抗制的历史概况
从中世纪末期一直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刑事审判是一种“争吵式”审判,即控辩双方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互相争辩。这种审判模式的主要目的是,让被告人本人在法庭上回应指控,以听取和检验被告人的陈述。之所以禁止律师代理被告人作庭审陈述,是因为:被告的反应“往往就能显露事实真相之一斑;而如果由其他人越俎代言,则真相可能不易彰显。”禁止律师代理陈述的理由,具体又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站在被告人的角度:“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可以像最好的律师一样,恰当地陈述事实”;“进行一项朴素、诚实的抗辩,并不需要技巧”,因为“一位问心无愧者,他的简明、单纯,他的毫无矫情的坦率言行,更能打动人心、更具有说服力,胜过其他当事人的滔滔雄辩”。另一方面是站在控方的角度,即担心若由出庭律师代理被告人陈述,会破坏被告的法庭信息源角色,掩盖犯罪事实:“如果饱学的律师可以代替被告诉答、提出抗辩,他们可能闪烁其词,巧言文过,损害证据,使真相难以大白,或需要更长时间。”概言之,确保被告人本人是庭审信息的最重要来源,是当时英国刑事诉讼的核心要务。这一时期的刑事审判制度展现的“争吵式”特征和被告人陈述特征,虽具有对抗制的影子,但因为没有律师参与,缺乏由律师主导的交叉询问等程序,所以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抗制。
但是从十七世纪末开始,在叛逆罪审判中,由于国王的控诉力量过于强大且经常出现伪证,为了保护作为被告的贵族的利益,辩护律师的角色被引入法庭。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辩护律师参与庭审的做法扩展到普通的重罪案件。开始由律师帮助被告人询问和交叉询问证人,但是禁止律师向陪审团陈述事实和解释证据,仍然要求被告人本人直接供述或辩解。随着律师参与的深化,其职能进一步强化,最终替代了被告:“通过阐明和运用控方负有举证和证明责任的原则,出庭律师基本上使被告噤声。这一变化催生了不自证其罪原则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律师职能的加强也使法官在庭审调查中成为消极的程序管理者,不再是积极的调查者或指导者角色。到十八世纪末,刑事审判基本上已由律师主导。原来的争吵式审判注重由被告人回应指控和证据,新的对抗式审判则强调由辩护律师检验和反驳指控。
随着争吵式审判模式的淡出,律师主导了对证人的询问:在使用污点证人的案件中,律师通过交叉询问提醒陪审团存在伪证的可能性;在有赏金的案件中,律师通过交叉询问提示注意赏金这一诱因。但十八世纪辩护律师的活动囿于交叉询问,法律限制其向陪审团直接陈词。对于这一限制,辩护律师通过各种方式规避。例如,他们在交叉询问中融入对事实的陈述,在法律问题的外表下提出事实主张等。到了1836年,这一限制被取消,辩护律师可以像控方律师一样向陪审团发表陈词。于是,英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一方面形成了对抗式举证模式,另一方面形成了言词论辩式庭审:“在典型的充分律师化的审判中,事务律师在开庭前收集和准备证据,出庭律师在庭上揭明事实,询问和交叉询问,提出法律问题。……在取证过程中,英格兰的法官‘对这一过程显得莫不关己’,被告在辩护中则无所事事,……几乎使被告可以一言不发。”至此,英国在中世纪末形成的被告陈述式审判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律师的角色以及确立相应的交叉询问等庭审规则,形成了现代的对抗制审判模式。
2.英国民事诉讼中对抗制的历史概况
英国民事诉讼中对抗制的发展历史与刑事诉讼有很大差别。刑事诉讼到十六、十七世纪尚无辩护律师参与,但是民事诉讼在此之前就已经稳固地由律师代理了。“在刑事案件中,存在互相对抗的律师是十八世纪后半叶一个创举,但是在民事案件中这早已经是常规之举。在瑞德的笔记所记载的民事案件中,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已经稳固地存在着。”从律师参与和主导诉讼程序的角度来说,民事诉讼很早就已经是对抗制模式了。但是现代的对抗制审判不仅要求律师的主导性角色,而且还要求言词论辩式的庭审方式。当时英国的民事审判程序却是书面化的,远远不是言词辩论式的。如前文所述,这体现在:重视书面证据,在最佳证据原则所统领的证据规则体系中文件优于言词,督促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固定交易过程;当事人以及其他具有利益牵涉的人,不具有证人资格,因此缩小了出庭证人的范围;对于出庭证人,注重其宣誓这一仪式而非交叉询问的程序。因为没有形成言词论辩式的庭审,交叉询问、证人弹劾等对抗制程序的典型表征也尚未具备,所以很难断言英国在十八世纪之前的民事诉讼中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对抗制模式。反而是刑事诉讼更早地采用了言词式庭审(“争吵式”审判)。
综上所述,在十八世纪之前,英格兰的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都不是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对抗制模式。而经过十八世纪的发展,它们都具备了下述典型特征:第一,由诉讼双方的律师承担搜集、提交和在法庭上展示证据的职能,即对抗式举证模式;第二,以言词论辩的方式组织庭审,律师频繁地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和在法庭上做出陈述。现代对抗制的这两个特征与排除规则的发展有非常紧密的关联——不仅为排除规则提供了程序驱动力,而且使它的功能发生了转型。
(二)对抗式举证与信息激励机制
对抗式举证模式体现了所谓的司法竞技主义理念:“当事人在他们所比赛的项目中以其自有的方式进行搏击,法官不进行干预”。诉讼被视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竞赛,他们为了赢得竞赛必然竭尽所能。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为了说服事实认定者相信其主张,会积极搜集、保存和提交最能够证明主张的证据;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为了反驳对方,也有足够动力提出反证。因此,在举证责任明确的情况下,对抗式举证程序本身就足以激励诉讼双方竞争性地搜集和提交证据,供法庭做出事实认定。法官消极中立,无需对举证过程进行额外干预。司法竞技主义表达了对于对抗式举证模式的信赖:正如自由市场会调节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人的行为,从而促进整体福利一样,对抗式举证也能调节追求胜诉利益的诉讼双方的行为,从而促进法庭发现真相。对诉讼双方的举证行为应当实行“自由放任”而不是“法律管制”。
然而,正如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会调节失灵一样,对抗式举证程序也会出现失灵,不能确保诉讼双方提交最有利于法庭发现真相的证据。对抗双方是从自己的诉讼策略出发,以追求胜诉为导向的。所以,对抗式举证程序可能人为地导致某些证据的流失。诉讼双方乐于提供有助于自己胜诉的证据,而不是有助于发现客观真相的证据。采用美国证据法学家戴尔·南斯的术语来说,对抗制只能激励诉讼双方提交胜诉策略意义上的最佳证据,而非“法庭认识论意义上”的最佳证据。“在对抗制程序中,陪审团获取由当事人双方及其律师筛选、管理和掌控的信息。陪审员并不是从一个努力展示所有信息或构建真相的中立渠道处获得信息的。它必须在带有倾向性的对抗性证据展示中构建出真相。”
概言之,在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形中,对抗式举证程序本身不足以保证最佳证据的提交:对于某项待证事实,举证责任的承担者能够提交多种证据形式;从自己胜诉策略的角度考虑,隐藏认识论上的最佳证据而提交其他替代形式更可取;对方当事人无法获得这一最佳证据,所以无法向法庭提出反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抗式举证及其司法竞技主义,难以保证法庭获得最佳证据和发现真相;相反,它会造成对最佳证据的隐匿,使法庭更加远离真相。南斯将对抗制的这种失灵称为过滤效应(filtering effect)和证据缺失(evidence missing)。过滤效应是指,诉讼双方及其律师为了胜诉会对自己收集到的证据进行筛选,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而隐藏对自己不利;这种过滤效应导致某些有助于法庭发现真相的证据缺失了。“在一个依赖诉讼双方引出证人、文件或其他作为证据使用的东西的诉讼制度中,任何一方都具有强烈的动机去收集证据并且过滤所收集到的证据,只提交给法庭支持自己这一方目标的证据。”因此需要通过排除规则矫正对抗式举证的失灵。
排除规则矫治对抗式举证的失灵,是通过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包含以下要点:首先,排除证据是一个潜在的制裁手段。将律师提交的证据排除,意味着否定了律师取证和举证行为的法律效果。这类似于我国学者总结的“程序性制裁”原理。其次,之所以排除律师提交的某些证据,施加程序性制裁,是为了反向调整律师搜集、保存和提交证据的行为,激励他们提交最佳的证据。最后,通过激励律师的举证行为,最终目标是保障法庭基于最充分、可靠的证据,最大限度地发现真相。在非对抗制的诉讼程序中,排除规则仅仅是一个信息筛选机制,这种机制通过减少“坏”的信息的方式优化庭审决策环境;而在对抗制诉讼程序中,排除规则还是一个举证激励机制,通过增加“好”的信息的方式优化庭审决策环境。尽管这两种机制都以排除证据为手段,但前者着眼于特定证据所具有的被高估证明力或引发偏见之危险性是否超过其证明价值;后者着眼于在特定证据之外是否有本来可以提交的更好的证据。
随着对抗式举证的确立,对抗制失灵导致的证据偏向性,超过了赏金猎人和污点证人等实践所引发的证据危险性;前者是系统性的,后者则具有偶然性。对抗式举证的这种偏向性,成为伴随普通法系诉讼模式始终的一个因素。对这个因素的担忧,为排除规则的发展提供了持续驱动力。在对抗式举证环境中,排除规则不仅是一种通过筛选信息来规制陪审团的机制,而且是一种通过制裁手段敦促律师举证的机制,或者称为信息激励机制。这种机制的确立,实际上引出了一个观察排除规则功能的新视角——“向前”的视角(ex ante),以区别于“向后”的视角(ex post)。
(三)言词论辩式庭审与论辩程序规则
在形成言词论辩式的庭审之后,排除规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动力。言词论辩式庭审要求在一个有限的时空条件下做出事实认定:时间的有限性即所谓的“集中审理模式”,庭审过程要保持连续和集中;空间的有限性即以法庭上展示的证据作为裁判依据,庭外信息以及在庭外制作的书面材料,原则上应被阻隔在事实认定者视野外。相比于不限定时间和信息来源的职权调查模式,这种言词式庭审更容易被某些证据误导。前述具有危险性的信息,以及对抗制律师提交的偏向性证据,更容易给这种环境中的事实认定者增加错误裁决风险。因为事实认定者是在有限的信息基础上和紧迫的时间压力下做出裁决的,法庭上展示的证据是其仅有的决策依据。也就是说,言词论辩式庭审放大了前述危险性信息、对抗式举证之过滤效应的影响,从而也强化了以排除规则管控证明过程的必要。但是言词论辩式庭审与证据排除规则之间的关联不限于此,还有以下三个重要方面:首先,庭审论辩模式要求原始证据来源受到当庭检验;其次,法庭上的论辩过程导致了对证据和推论的原子式拆分;最后,异议-裁定机制衍生出对刚性化、一般性法律规则的需求。
1.对原始证据来源的当庭检验
言词论辩式庭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要求对原始证据来源的可信性进行当庭检验。这种当庭检验要求,衍生出对证人的“亲身知识”(personal knowledge)要求。亲身知识是指证人直接感知到的一手信息,与亲身知识相对的,是传闻和意见。因为传闻是对目击证人亲身知识的转述,传闻证人对于作证事项无亲身知识;意见证言是在亲身知识的基础上做的进一步推断、概括或评论,不是对案件事实的直接反映。传闻和意见证言都将原始信息来源隐藏了,使律师和事实认定者无法对其可信性进行当庭检验。因此传闻排除规则和意见证言排除规则都可以看作旨在确保当庭检验原始证据的规则。
尽管亲身知识要求及其派生出来的传闻规则和意见规则,表面上看来只是针对证言这一证据种类,但实际上可以辐射到几乎所有的证据。因为,在英美证据法中,有一个普遍性的要求,就是所有的证据都应当由特定的证人证言进行“担保”(vouch)。证人证言不仅是一个具体证据种类,实际上还是几乎所有证据种类的呈现方式。“几乎所有的证据,如果它本身不是一个出庭证人的当庭证言,那么需要由这样的一个出庭证人将它呈现给法庭。”即所谓“由证言担保非言词证据的假定”。一个例子就是对于物证和书证的“鉴真”要求:通常应当由收集和保管证据的人出庭说明情况,这是物证和书证被采纳的前提条件。所以,证人亲身知识要求以及相应的排除规则,实际上会关涉到所有的证据种类,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证据可采性要求。
言词论辩式庭审重视对原始证据来源的当庭检验,由此衍生出排除规则。这种观点也包含在英美学者对交叉询问和传闻规则之间关系的理解中。交叉询问证人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当庭检验证据的机制。“交叉询问对方证人的机会对于一个公正的对抗制检验程序来说,被认为是基础性的,因为交叉询问能够暴露证言中的虚假、弱点和不一致。”法学者们经常援用威格莫尔的说法强调交叉询问的重要性:它是“我们曾经发明的揭示事实真相之最伟大的法律引擎。”主流的英美证据法理论认为,正是为了保障交叉询问这种证据检验机制,才确立了一套复杂的传闻排除规则。代表性的论述如:“传闻证据被假定为不可采,因为通常证人必须亲自到庭作证,这样他们可以在做出陈述的时候被交叉询问。”
2.对证据和推论的原子式拆分
言词论辩式庭审程序,尤其是其中的直接询问-交叉询问机制和异议-裁定机制,直接导致了对证据和推论的原子式拆分,而这种拆分为排除规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英美言词论辩式庭审区别于大陆法系庭审的一个技术性特征是,它以一问一答的方法而不是整体陈述的方法引出证言。向事实认定者展示证人证言,有赖于律师的逐次提问。这种提问方式,将一个完整、连贯的陈述拆分成微小的信息单元,以原子化的方式呈现给事实认定者。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都具有这种技术性特征。即时提出异议的庭审论辩技巧,也必须聚焦于细微的信息点。提出异议的对方律师必须表明是对哪一个信息点存在何种异议。进一步来说,由提问和异议而导致的原子化拆分,实际上不仅是针对证据,而且还针对由证据到事实的推论。提出异议的律师,异议的理由可以细化为反对从一项证据作出某个特定的推论,而不是反对从这个证据出发的所有推论。
这种原子式拆分对于排除规则的发展非常有意义。因为,所有的排除规则都是排除某个具体的信息,而不是由多种信息构成的整体。更进一步说,排除规则实际上是排除某种特定的推论(为了特定目的而使用该证据),而不是排除根据某个证据可能作出的所有推论(为了所有目的而使用该证据)。传闻排除规则、品格排除规则、意见排除规则等,都是以对证据和推论的原子式拆分为基础。对于英美证据法的这种原子化特征,美国学者兰博斯道夫以其他术语进行了描述:“证据课堂上的学生所学到的,主要是一种特别化(particularization)的方法。证言被以逐个问题的方式进行考虑,每个问题又被以逐个推论的方式进行考虑。另外,陪审员也被假定为采用特别化的方法,因此能够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考虑某个给定的证据,但忽略该证据的其他用途。”言词论辩式的庭审所导致的原子式拆分,与排除规则的原子化特征是非常一致的。当然,很难清晰地界定谁是因谁是果,但是可以断言,言词论辩式庭审能够很好地在技术性层面上契合、支撑和推动排除规则的运行。
3.对刚性化规则的需求
前文分析了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管制事实认定者的方式,相对于其他管制方式的优势。言词论辩式庭审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比较优势,因为它要求建立一种刚性化、一般化的管制,而不是裁量性、个案式的管制。言词论辩中包含着“异议-裁定”机制:诉讼双方的律师互相反驳对方的举证和提问,在法庭上即时提出异议;对于这些异议,法官需要即时地裁定支持或者否决。这种法庭上的即时互动,在以下几个方面突显了排除规则的优势:首先,提出异议与作出裁定都需要法律理由,而预先设定的排除规则能够提供这种理由。援引排除规则为据的异议和裁定,使法庭上的言词论辩得以有序进行。其次,即时的异议和裁定有便捷性要求。法官适用排除规则,就是从一事一议的管制变成了一般化、常规性的管制,后者在整体上更有效率。而上文描述的法官组织证据展示、质询控方证人、概括和评论证据、舍弃陪审团裁决等,都属于一事一议的管制方式。再次,当包含异议和裁定机制的言词论辩式庭审成为律师和法官的工作常态后,就产生了对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传播需求,排除规则以及相关的教义学知识满足了这种需求。最后,以异议和裁定机制为特征的言词论辩式庭审,要求法官保持消极、克制的程序管理者姿态,而不是作积极、主动的干预者,律师则应当成为主导法庭论辩的主体。排除规则的适用方式契合了这种对法官、律师的角色设定。可以看出,在言词论辩式庭审环境中,排除规则不仅具有影响事实认定的实质功能,而且本身还发挥了程序性的功能,成为一套预先设定的论辩程序规则。
六、中国诉讼程序与证据排除规则立法
上文的制度史叙事说明,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英格兰牢固确立和持续发展,是为了回应诉讼程序与司法实践的一系列变动。这些变动从不同侧面为排除规则提供了发展的动因:首先,陪审团的转型造就了二元管控结构和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这为排除规则的发展确立了制度空间。其次,证据成为危险性信息源,以及其他管制方式的式微,产生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实践需求。最后,激励对抗式举证和支撑言词论辩式庭审的需要,成为排除规则得以长远发展的程序驱动。这种法制史角度的分析,揭示了排除规则的制度功能和运行机制。以此为基础,本部分回到中国法制和司法改革语境。当代中国的诉讼程序也处在变动之中,这主要是司法改革的结果。例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庭审方式改革,推动了职权主义的弱化和对抗制因素的加强;目前的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法官员额制与责任制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等,使得诉讼中的权力结构、程序模式持续变动。在这些背景下,沿循上文的论述层次和结构,下文简要分析排除规则在中国是否具备充分的发展动因。
第一,二元管制结构问题。既然排除规则是一套管制司法证明的体系,那么必须要存在“管制-被管制”的二元结构。英格兰从1220年左右就开始采用陪审团解决事实问题,因此这种管制结构是一个古老的普通法传统。但是中国的法制传统中不存在法官管控陪审团的结构。即使在有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案件中,陪审员也只是合议庭的组成人员,而不是与法官分席而坐、分工裁决的独立主体。尽管如此,中国的司法制度中可能存在其他意义上的二元管制结构。首先,有权制定证据规范性文件的法院,与具体承担裁决职责的合议庭或法官之间,存在管制关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多个关于审查判断证据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目的是对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工作进行管控和指导。因此,在法院系统内部,甚至在同一个法院内部,存在着一种管制结构,这种管制结构导致了一些证据排除规则的生成。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文件和省高院的规范性文件中发现大量证据排除规则,它们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正式立法。其次,法官的心证公开与事实论证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二元管制结构的替代机制。与陪审团裁决事实的制度不同,我国法官审模式要求法官公开其心证且对此予以论证。法官不仅要自由地“形成”心证,而且要事后“审查”自己的心证,这种审查还受到二审、再审程序的制约。这就意味着,法官要站在一个外部的、中立的立场管制、约束自己的心证,确保这种心证符合人际化的(主要是法官共同体的)理性标准。这种自我管制结构能够给证据排除规则留出一定空间。因为如果法律要求排除某项证据,就意味着法官在事后审查心证时应自觉忽略这项证据,而且在论证其裁决时不得用这项证据作为论据。但这种管制结构上的替换,可能会带来排除规则的功能转变——从信息阻隔机制转换成论证禁止机制。最后,随着庭前会议和人民陪审制改革的推进,中国诉讼程序可能会逐渐发展出英美法意义上的二元管制结构。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创设的庭前会议制度,旨在将某些程序性事项(包括证据排除问题)与实体审理相分离。如果这种程序上的分离能够严格贯彻、不断推进,就可能导致证据采纳或排除问题与事实认定问题的分离(既包括阶段上的分离也包括裁决主体的分离)。从2015年开始试点、2018年通过立法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以建立大合议庭陪审模式为愿景,吸纳了一些英美陪审团制度的要素性特征,强化了法官与陪审员之间的指导、管控关系。当然,二元管制结构的牢固确立,还有待庭前会议制度和陪审制度等改革实践的进一步推进。
第二,事实认定者的劣势地位问题。事实认定者必须处在一个相对劣势的地位上,才存在实施管制的可能性。这种劣势地位一方面来自对其认知能力的假设——不够理性的事实认定者;另一方面来自庭审制度形态——非知情裁判模式。如上文所述,英美证据法理论中关于陪审员认知能力的拙劣假设,满足了前者;十六世纪英格兰陪审团的转型,满足了后者。但是中国的诉讼程序是否也具备这两个条件?首先,认知能力假设。英美证据理论研究者在阐述这个条件的时候,过于聚焦在对陪审团与法官的能力比较上。实际上,也可以不采取比较的方式,而是对法官和陪审团都作出如下假定:他们都是大致上理性的事实认定者,但都具有某些需要防范和矫正的非理性认知倾向。这一假定符合经验常识,不必陷入到对法官和陪审团孰优孰劣的争论之中。当然,法官和陪审团之间的诸多差别,会成为一个影响该假定之范围和程度的变量,但是不会导致该假定的完全无效。具体到中国法官,作出以下假设也是合理的:法官有可能高估某些证据的证明价值,或者被某些证据引发不公正的偏见,因此有必要对此予以规制。法官是关于法律问题的专家,而不是关于事实问题的专家;在事实推理方面,法官分享了普通人的理性,也共有普通人的认知弱点。其次,非知情裁判。在职权主义风格浓厚的庭审程序中,法官处在很明显的信息优势地位上,可以自主调查取证和到庭外核实证据。这种模式与英格兰十六世纪以来形成的陪审团非知情裁判差别很大。因为后者将陪审团可用的信息限定于法庭上出示(而且是格式化地出示)的证据,不仅禁止陪审团成员借助庭外信息裁判,而且禁止他们在法庭上自主询问和调查。另外,卷宗主义的庭审也迥异于陪审团的非知情裁判,因为前者使得法官在开庭前通过阅卷形成对案件事实的预断,而不是完全根据法庭上的信息认定事实。中国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通常被认为具有职权主义和卷宗主义风格,看起来与英美陪审团的裁判结构差别很大。但是,以下制度改革动向也表明,中国的诉讼程序在强化非知情裁判特征:首先,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承接了上世纪末的庭审方式改革,旨在推动庭审实质化和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其次,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区分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造成了陪审员与法官的相对分工,其中的陪审员会成为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非知情裁判者。
第三,对抗式举证问题。在十八世纪英格兰诉讼程序中,排除规则体系的快速增长是为了迎合一个实践需求,即管控输入法庭的那些具有危险性的证据种类。这与当时英格兰的赏金猎人、污点证人等具体司法实践有关。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当然与彼时的英格兰有很大差别,但是中国的诉讼程序同样面临着危险性信息源的问题,这主要是现代对抗式举证失灵造成的。在中国诉讼程序中,证据排除规则同样可以发挥信息激励功能。首先,中国的诉讼程序基本上是一种对抗式举证模式,主要依赖诉讼双方搜集和提交证据。尽管保留了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规定,但是绝大多数庭审证据是由诉讼双方提供的,法官取证只是补充性的。其次,这种对抗式举证会造成过滤效应和证据缺失问题。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和律师以及刑事诉讼辩方都追求胜诉,经常偏离法庭发现真相的目标。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尽管作为公共机构负有所谓的“客观义务”,但是因为诉讼角色、绩效考核以及许多程序外因素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具有偏向性,可能会片面追求控诉成功率,怠于搜集和提交无罪与罪轻证据或刻意隐藏这类证据。最后,排除规则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信息激励机制。既然中国诉讼程序中的对抗式举证也会失灵,就有必要通过排除规则来激励举证。例如,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法院通知检察院提交其已收集但未入卷的、有利于辩方的证据,但是没有规定在检察院拒绝提交之后法院可以采取的制裁手段。针对这种情况,以及检察院拒绝提交“最佳”证据的其他可能情况,设置排除规则(即排除针对同一待证事实而提交的其他证据,视为检察院未履行对这一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可以给检察院的举证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
第四,言词论辩式庭审问题。按照上文的分析,普通法系的言词论辩式庭审与排除规则有密切联系:首先,言词论辩程序要求对原始证据进行当庭检验,排除规则能够敦促具有亲身知识的证人、对实物证据有鉴真义务的证人出庭,从而满足当庭检验要求;其次,言词论辩的过程导致对证据和推论进行原子化拆分,这为排除规则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因为它们所适用对象正是原子化的证据和推论;最后,庭审中的异议-裁定机制要求确立刚性化、一般化的论辩程序规则,证据排除规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具有异议和裁定的正当性、适用的便捷性、在法律共同体内的可传播性、与法官和律师庭审角色的契合性等制度优势。中国的审判程序与这种言词论辩式庭审模式有许多悖离之处。例如,庭前阅卷、庭后查阅庭审笔录、庭外调查核实证据对于裁决案件具有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庭审言词论辩的意义;法官在法庭调查中的职权主义姿态,压缩了律师的言词论辩空间;没有设置区别于直接询问的交叉询问规则,一律禁止律师采用诱导性方式发问等。目前的这种庭审方式难以为排除规则的运行提供强大驱动力。但是如果从动态角度观之,庭审实质化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求强化庭审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在法庭调查中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如果随着改革的推进,言词论辩式的庭审风格逐渐强化,就会为排除规则的运行提供有力的程序驱动机制。
第五,管制方式的比较优势问题。证据排除规则只是管制司法事实认定活动的方式之一,在普通法的历史上它与其他管制方式相竞争,最终取得了比较优势。在当代中国的证据规则体系中,除了排除规则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的管制方式:中国法中存在许多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随着陪审制改革的推进,可能会衍生出法官概括和评论这种规制方式,以及法官事后推翻陪审员裁决的方式;法官依职权取证和到庭外调查核实证据,也可以看作是对诉讼双方之证明活动的补充和矫正。与这些管制方式相比较,排除规则能否具有足够的优越性,从而形成规模化的体系,取决于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将如何展开。尤其是取决于,我们将会如何塑造法官、律师、陪审员的庭审角色。如果最终形成作为消极程序管理者的法官、积极主导证明过程的律师、终局性地裁决事实问题的陪审员角色,那么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司法程序中,就可能像在历史上的英格兰司法程序中那样,成为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管制司法事实认定的方式。
本文的分析表明,证据排除规则这种源于普通法系的规范类型,在中国诉讼程序中的适用性取决于许多具体的诉讼结构特征。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所带来的诉讼程序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这些特征,为排除规则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动力。但是尚未形成非常完备的程序结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文件中已经存在一些零散的排除规则,但是它们尚未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本文的分析进路主要是新功能主义或结构-功能主义的比较法。“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新功能主义进路从这一基本论断出发认为比较法要想了解法律的复杂性,就必须与整体的法律文化结合起来,将法律的技术专长和文化认识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方法论框架下,排除规则这种对司法事实认定的管制手段不具有天然的跨法系普适性,而是取决于它与具体语境下的司法程序以及宏观制度环境之契合性。中国司法程序是否为排除规则提供了强劲的动因,从而使得这种立法形式成为一种有效的调整司法证明的方式,由于诉讼程序的持续变动而仍有很大的开放性和讨论空间。
参考文献:
1 这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401、402条款对相关性的界定。中国法中不存在这样的明确表述,但是证据定义条款中包含了相关性要求。《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可以用于证明”应当视为对相关性的要求,与“任何倾向性”标准实质上相同。
2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403条款明确表述了这类理由:“如果下述一项或多项危险性在实质上超过了一项相关证据的证明价值,则法庭可以将该证据排除:不公正的偏见,混淆争点,误导陪审员,不当拖延,浪费时间,或者不必要地提交累积证据。”该理由实际上是许多证据排除规则背后的基本原理。《联邦证据规则》“立法咨询委员会注释”(Notes of Advisory Committee on Proposed Rules)对此解释道:“遵循这一条款的众多规则,是针对具体情况的个别应用。然而,它们反映了这条规则背后的政策。这条规则旨在指导处理许多尚未被制定具体规则的情况。”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e/rule_403,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5日。中国法中要求提交书证原件和物证原物的规则、针对鉴定意见的有限传闻排除规则、意见证据排除规则等,也是基于“证明价值-危险性权衡”理由。
3 这三个规则分别参见《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88条、《民事诉讼法》第65条。
4 证明政策规则(rules of probative policy)、外部政策规则(rules of extrinsic policy)的划分,源于威格莫尔。他将证明政策规则进一步分为相关性要求(relevancy requirements)和附属的证明政策规则(rules of auxiliary probative policy),对应于本文的第一类、第二类理由。See John H. Wigmore, 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 (Peter Tillers ed.), vol. 1,Boston: Little Brown, 1983,p.689.达马斯卡基本上延续了威格莫尔的分类,但是采用了“外部规则”(extrinsic rules)和“内部规则”(Intrinsic rules)的表述。参见(美)米尔建·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艾伦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将诉讼效率目标单列,采用了三分法:促进准确性的规则、提高效率的规则、保护外部政策的规则。参见(美)罗纳德•艾伦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第三版),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5 因此塞耶认为:“相关性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塞耶是在批判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证据法学家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的,斯蒂芬将证据法统括在相关性规则之下。参见(英)威廉·特文宁:《反思证据:开拓性论著》,吴洪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6 相关分析参见米尔建·达马斯卡,见前注〔4〕,第16-23页。
7 Terence Anderson, David Schum and William Twining, Analysis of Evid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
8 对英国简化排除规则体系的描述和分析,see Alex Stein, Foundations of Evidenc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7.
9 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法典化运动,使这类规则从普通法上升为体系化的成文法。这些成文证据法典以排除规则为主体,未表现出松动的趋势。关于该法典化运动的介绍,参见易延友:“证据规则的法典化”,《政法论坛》2008年第6期,第80页。
10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1 陈瑞华:“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第92页。
12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保生主编:《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 Holmes, J., N. Y. Trust Co. V. Eisner, 256 U. S. 345, 349. 转引自(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2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进行的法制史考察并非描述彼时的法律文本或者法律教义,而是分析推动生成这些文本、教义的因素。本文将援引英美学者的描述性法制史研究成果,基于对这些成果的分析,解释和论述排除规则的发展动因。因此本文的研究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解释性的。关于“描述性法史学”和“解释性法史学”的区分,参见胡旭晟:“描述性的法史学与解释性的法史学——我国法史研究新格局评析”,《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第38-43页。
14(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15 John H. Wigmore, Wigmore on Evidence: A Students’ Textbook of the Law of Evidence, The Foundation Press, 1935, p.5.
16 John H. Wigmore,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ules of Evidence”, in Select Essays in Anglo-American Legal History, Volume 2,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 1908, p.696.转引自John H. Langbein,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Evidence: A View from the Ryder Sources”, Columbia Law Review,Vol.96,No.5, 1996, p.1171.
17 郎本对上述文献的考证和分析,包含在他的以下成果中:ibid., at 1168-1202; John H. Langbein, “The Criminal Trial before the Lawyers”,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45,No.2, 1978,pp.263-316; John H. Langbein, The Origins of Adversary Criminal Tri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 吉尔伯特的《证据法》成书时间为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瑞德法官的笔记制作时间为十八世纪五十年代,老贝里法庭审判实录跨越的时间很长,但是郎本主要考察了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内容。
19 Gilbert, The Law of Evidence(7th), Philadelphia: Joseph Crukshank,1805, p.3. 这种最佳证据理论在当时是被广泛接受的。实际上在吉尔伯特出版专著前就已存在这种理念。有文献表明,在1700年代的一个案件中,霍尔特(Holt)大法官断言:“审判中惟一需要的证据是就事物的本质而言所能产生的最好的证据。”Sopinka and Lederman, The Law of Evidence in civil Case, Butterworths, 1974, p.278. 转引自易延友:“最佳证据规则”,《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6期,第97页。
20 Stephan Landsman, “From Gilbert to Bentham: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Evidence Theory”, Wayne Law Review, Vol.36, 1990, p.1154.
21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16, p.1181.文中提出:“在民事诉讼中,这种偏好书面文件证据的规则之潜台词是:谨慎的人们要将交易事务制作成封印文件,因为封印文件胜过相反的主张……延续至达德利·瑞德时代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有数个世纪之久的倾向,即在民事陪审团审判中抑制对口头证据的使用。”at 1183.
22 Ibid., at 1184.
23 Stephan Landsman, supra note 20, pp.1156-1157.
24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16, p.1187.关于在当时的民事审判中使用传闻证据的例子,参见文中第1186-1188页。
25 See John H. Langbein, “The Criminal Trial before the Lawy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45, No.2, 1978, pp.289-291.
26 关于具体的案件例子,see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16, pp.1191-1192.Ibid., at 1193.
27 Stephan Landsman, supra note 20, pp.1156-1157.
28 See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16, pp.1188-1189.
29 郎本详细考证了品格证据排除规则、非自愿口供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的渐进式发展。(1)尽管在1684年和1692年的案件中就已经出现排除品格证据的做法,但是在1714年之前,法庭实际上很少提及该规则。在1714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法庭也并未严格地执行该规则。只有到1770年之后,品格证据排除规则才开始被严格执行,关于被告人品格的证据被阻止进入法庭。(2)要求排除非自愿口供的规则,在18世纪40年代的案例中被提出,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采纳非自愿口供或者采纳后做出提醒指示的做法。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时间里,排除非自愿口供的做法逐渐胜出,成为常规做法。1769年的案例显示,排除非自愿口供已经成为刚性的规则,不容法官自由裁量。(3)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关于法庭拒绝传闻证据的案例记载。但是在整个十八世纪,传闻证据未经异议即被法庭接受的例子比比皆是。到十八世纪末才在刑事审判中牢固地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直到1789年,才出现以“无法交叉询问”为理由排除传闻的判例。参见(美)约翰·郎本:《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起源》,王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198、209-212、220-224页。
30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16, p.1194.
31 参见威廉·特文宁,见前注〔5〕,第70页。
32 John H. Wigmore, supra note 4, p.632.
33 Bernard Grofman and Heathcote Wales, “Modeling Juror Bias”, Legal Theory, Vol.5, 1999, p.224.
34 罗纳德•艾伦等,见前注〔4〕,第99页。
35 See Lisa Dufraimont, “Evidence Law and the Jury: A Reassessment”, Mcgill Law Journal, Vol.53, 2008, pp.220-221.
36 米尔建·达马斯卡,见前注〔4〕,第64页。
37 对这种逻辑矛盾的分析,see Dale A. Nance, “The Best Evidence Principle”, Iowa Law Review, Vol.73, 1987, p.271.
38 当然,证明陪审员认定事实的某些优势和劣势的研究结论都存在。但是一般性地预设陪审员是拙劣的事实认定者,缺乏足够的现代认知科学和实证研究根据。参见樊传明:“陪审员裁决能力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2期,第91页。
39 Edmund M. Morgan, “The Jury and the Exclusionary Rules of Evid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4, No.2, 1937, p.248.
40“控制陪审团”和“控制律师”的表述,来自戴尔·南斯的论文,see Dale A. Nance, supra note 38, p.229.尽管威格摩尔强调英美证据法与陪审制的关联,但同时也承认证据法与对抗制的联系:“英国证据制度的区别性特征,主要归因于在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衡平法院的案件除外)中使用陪审团,其次归因于在法律程序中普遍的公平竞争或者说‘真实竞赛’这一独特的英国精神。”John H. Wigmore, supra note 15, p.4.
41 达马斯卡认为,南斯是“普通法证据制度首先也最主要是对抗制的产物”这种理论“在当代颇有创见的解释者”。参见米尔建·达马斯卡,见前注〔4〕,第3页。
42 详细论述see Dale A. Nance, supra note 38, pp.263-270.
43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16, p.1201.
44 关于类型研究进路的讨论,参见米尔建·达马斯卡,见前注〔4〕,第3-9页。
45 达马斯卡对这种结构及其与英美证据法之间关系的分析,参见米尔建·达马斯卡,见前注〔4〕,第64页。加拿大学者丽莎·达夫瑞蒙特对证据法与陪审团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综述。See Lisa Dufraimont, supra note 36, pp.220-233.
46 当然,如果往前追溯,能找到更为久远的陪审团制度的原始形态或者说观念萌芽,甚至可以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找到类似的观念。但是若以有可靠法制史文献记载为标准,则追溯到王室证人制度更为恰当。
47 英国的这种制度到底是起源于诺曼、斯堪的纳维亚、法兰克还是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律,存在争论。See Ralph Turner, “The Origins of the Medieval English Jury: Frankish, English, or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7, No.21968,pp.1-10.对这种制度在英国的情况的介绍,参见(美)詹姆士·惠特曼:《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根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201页。
48 詹姆士·惠特曼,同上注,第201-202页。
49 惠特曼认为英国知情陪审团制度的起源与神明裁判的衰落有直接关系。根据他的研究,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圣会,将神明裁判视为“血腥判决”,禁止神职人员再参与这一程序。这导致了神明裁判制度的式微,督促欧洲各国寻找替代性的审判方式。英国找到的替代性方式就是知情陪审团制度。同上注,第187-190页。
50 MacNair, “Law, Politics, and the Jury”, Law and History Review, Vol.17, No.3 1999, p.603.
51 Charles A. Boston, “Some Practical Remedies for Existing Defect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61, No.1, 1912, pp.11-13. 转引自(美)伦道夫·乔纳凯特:《美国陪审团制度》,屈文生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52 See Dale A. Nance, supra note 38, p.271.
53 美国学者惠特曼认为,英美法系之所以会形成陪审团制度,是因为宗教性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为了使法官避免因裁决被告有罪而受“鲜血之污”。因此陪审团制度在产生之初是一个“道德慰藉”程序,而不是“事实证明”程序。参见詹姆士·惠特曼,见前注〔48〕,第186页。
54 陪审团制度除了涉及准确认定事实这个目标之外,还具有以下价值:陪审员可以代表社会的价值观,使法律以较为缓和的方式适用,避免个人受到政府权力的过分压制;陪审团制度可以让普通人直接参与司法,从而起到法治教育功能;它还有利于增强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对陪审团制度价值的概括,see Lisa Dufraimont, supra note 36, pp.208-213.
55 John H. Wigmore, supra note 15, p.5.
56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16, p.1168.
57 John H. Wigmore, supra note 15, p.4.
58 William W. Blum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rected Verdict”, Michigan Law Review, Vol.48, No.5, 1950, p.558.
59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16, p.1171.
60 John H. Wigmore,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ules of Evidence”, in Select Essays in Anglo-American Legal History, Volume 2,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 1908, p.692.转引自ibid., at1171.
61 John H. Wigmore, supra note 15, p.4.“非知情人裁判”这一术语,借鉴自吴宏耀:《诉讼认识论纲——以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威格莫尔将这种陪审团称为“指示型陪审团”。
62 See ibid., at5.Ibid., Wigmore, at 4-5.关于赏金猎人制度的介绍,参见约翰·郎本,见前注〔30〕,第134-139页。
63 同上注,第139-143页。
64 John H. Langbein, The Origins of Adversary Criminal Tri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p.148-165. 转引自Lisa Dufraimont, supra note 36, p.238.
65 See Edward J. Imwinkelried, “The Worst Evidence Principle: The Best Hypothesis as to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Evidence Law”,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Vol.46, No.5, 1992, pp.1069-1099.
66 关于“玛丽式审前程序”以及治安官制度的介绍,参见约翰·郎本,见前注〔30〕,第28-31页。
67 当时未形成严格的证明责任机制,被告人尚未享受到“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保护,因此更加剧了这些危险性信息源可能带来的损害。在十八世纪初,现代刑事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机制尚未完全成型。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与十八世纪辩护律师的出现息息相关。被告没有辩护律师,行使沉默权就意味着全盘放弃辩护权。关于“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在十八世纪最终确立的历史,参见詹姆士·惠特曼,见前注〔48〕,第286页。
68 约翰·郎本,见前注〔30〕,第13页。
69 同上注,第20页。
70 对法官评论和概括的介绍,参见罗纳德•艾伦等,见前注〔4〕,第843页。
71 See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25, pp.289-291.
72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16, p.1193.
73 但是现代民事陪审团审判也会要求陪审员做出具体裁决,回答法官的问题清单。参见陈学权:“刑事陪审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第61页。
74 相关介绍参见伦道夫·乔纳凯特,见前注〔52〕,第366页。
75 See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25, pp.289-291.
76 John H. Wigmore, supra note 15, pp.4-5.
77 William Hawkins, A Treatise of the Pleas of the Crown (2 vols.), London 1716, p.400.转引自约翰·郎本,见前注〔30〕,第3页。禁止辩护律师参与案件事实问题,是一个在英格兰刑事诉讼中延续了数个世纪的规则。该禁令仅适用于重罪案件,而且只针对事实问题,不包括法律问题。在理论上,刑事被告人可以聘用律师提出法律争议,特别是在审前的讯问或诉答阶段。参见约翰·郎本,见前注〔30〕,第19页。
78 同上注,第24页。
79 同上注,第6页。
80 同上注,第297页。
81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16, p.1201.
82 美国法学家庞德1906年在美国律师公会演说时阐述了司法竞技主义的理念。参见徐昕:“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的均衡分配——兼论民事诉讼的本质”,《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第74页。
83 达马斯卡在概述两大法系证明程序的趋同和差异时,用“自由放任”和“法律管制”这两个经济学术语比喻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程序的特征。参见(美)米尔建·达马斯卡:“两大法系错误区别中残留的真相”,刘派译,《证据科学》2012年第4期,第88-97页。
84 南斯区分了两种最佳证据概念:认识论的最佳(epistemically best)和反讽的最佳(cynically best)。后一种意义指的是从一方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对于他的案件最有证明力的证据,而实际上对事实认定者持一种反讽态度,因为这不是从最有利于事实认定者发现真相的角度考虑的。See Dale A. Nance, supra note 38, p.240.
85 伦道夫·乔纳凯特,见前注〔52〕,第239页。
86 Dale Nance, “Missing Evidence”, Cardozo Law Review, Vol. 13, 1991, p.831. 按照戴尔·南斯的分析,在对抗制程序中有四种证据缺失的情况:1.未发现证据,即诉讼双方都没有发现某个确实存在的证据;2.不提交证据,即诉讼双方都知道存在某个证据,并且都能提交,但他们都选择不提交;3.压制证据,即某个证据对于诉讼一方是有利的,但另一方控制着这个证据并且拒绝提交;4.排除证据,即有法律规则禁止提交某种证据。南斯详细分析了这几种情况在对抗制中的成因以及备选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关注“压制证据”的情况。“未发现证据”是一个取证技术和能力的问题,“不提交证据”主要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排除证据”则是法律为了实现某些目标而故意为之。“压制证据”体现了对抗式举证程序的失灵。
87“程序性制裁是通过宣告无效的方式来追究程序性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88 关于最佳证据原理以及排除规则激励举证效应的详细分析,see Dale A. Nance, supra note 38, pp.240-247.
89 美国学者鲁伯斯道夫区分了考察证据法的两种视角:一种是被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向后”的视角(ex post),即“站在要决定是否采纳当事方所提交证据的法官的立场上来思考”,主要关注的是,某项证据的误导性、对外部政策的损害以及对时间的浪费是否超过其证据价值,并据此采纳或排除证据。另一种是“向前”的视角(ex ante),即考虑“证据法如何影响关心并参与诉讼的当事方的行为”,关注证据法可能给庭审前的行为(尤其是搜集、保存、提交证据的行为)所带来的激励或抑制作用。See John Leubsdorf, “Evidence Law as a System of Incentives”, Rutgers School of Law-Newark Research Papers, No.065,p.1.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566974, 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5日。
90 美国学者兰兹曼也认为,在十八世纪末,证据评价的方法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强调当庭的、言词的证据之意义;依赖交叉询问程序评价证据,而不是依赖以前的那种以形式要件(如宣誓、封印)为标准的评价方法。See Stephan Landsman, supra note 20, pp.1150-1151.
91 John Leubsdorf, “Presuppositions of Evidence Law”, Lowa Law Review, Vol.91, 2006, p.1234.
92 关于鉴真规则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罗纳德•艾伦等,见前注〔4〕,第212页。
93 R. v. Lyttle, 2004 SCC 5, [2004] 1 S.C.R. 193 at paras. 1, 41-43, 234 D.L.R. (4th) 257 [Lyttle]. 转引自Lisa Dufraimont, supra note 36, p.236.
94 张保生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95 R. v. Khelawon, 2006 SCC 57, [2006] 2 S.C.R. 787, 274 D.L.R. (4th) 385. 转引自Lisa Dufraimont, supra note 36, p.237.
96 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404条款所规定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为例。法律只是禁止使用品格证据“证明某人在特定场合下的行为与其品格具有一致性”,但是可以使用品格证据“证明动机、机会、意图、准备、计划、明知、身份,或者证明无过失或意外事件”。
97 John Leubsdorf, supra note 94, p.1213.
98 从《立法法》的角度来看,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不无疑问。《立法法》第104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证据司法解释,经常是在创设新的规则,而不是对已有法律规则的具体应用性解释。而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在本省范围内适用的证据规范性文件无《立法法》依据。
99 最典型的内容就是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在七人大合议庭模式中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问题。《人民陪审员法》第22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
100《人民陪审员法》第20条就体现了法官对陪审员认定事实工作的指导和管控:“审判长应当履行与案件审判相关的指引、提示义务,但不得妨碍人民陪审员对案件的独立判断。合议庭评议案件,审判长应当对本案中涉及的事实认定、证据规则、法律规定等事项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向人民陪审员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101 例如,对于被告人非自愿的供述、关于被告人不良品性的证据、比较血腥的证据等,陪审团成员因为缺乏法律实践经验而确实更容易产生偏见;法官因为长期从事审判形成了职业化思维,能够较好地防范这些证据引发的偏见。所以针对这些证据设定排除规则是符合“控制陪审团”理论的。参见米尔建·达马斯卡,见前注〔4〕,第40-43页。
102 对“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政策的分析,参见樊传明:“审判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分析及其解决”,《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192页。
103 理论上认为,检察官负有“客观义务”,即“检察官超越控方立场,坚持客观公正”。参见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检察官客观义务”,《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75页。
104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39条:“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105 对这类规则的描述和分析,参见李训虎:“证明力规则检讨”,《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56-173页;陈瑞华:“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47-163页。
106 这些规制方式在《人民陪审员法》第20条、第23条第二款中有一定体现。
107 郑智航:“比较法中功能主义进路的历史演进”,《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3期,第13页。
本文原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


下一篇:最后一页
